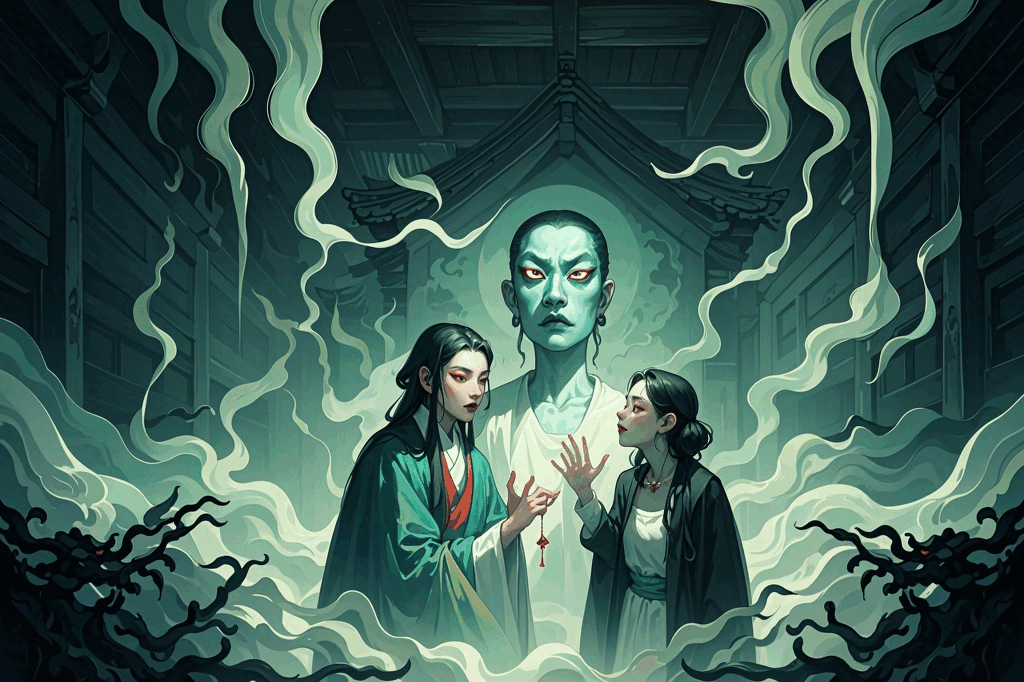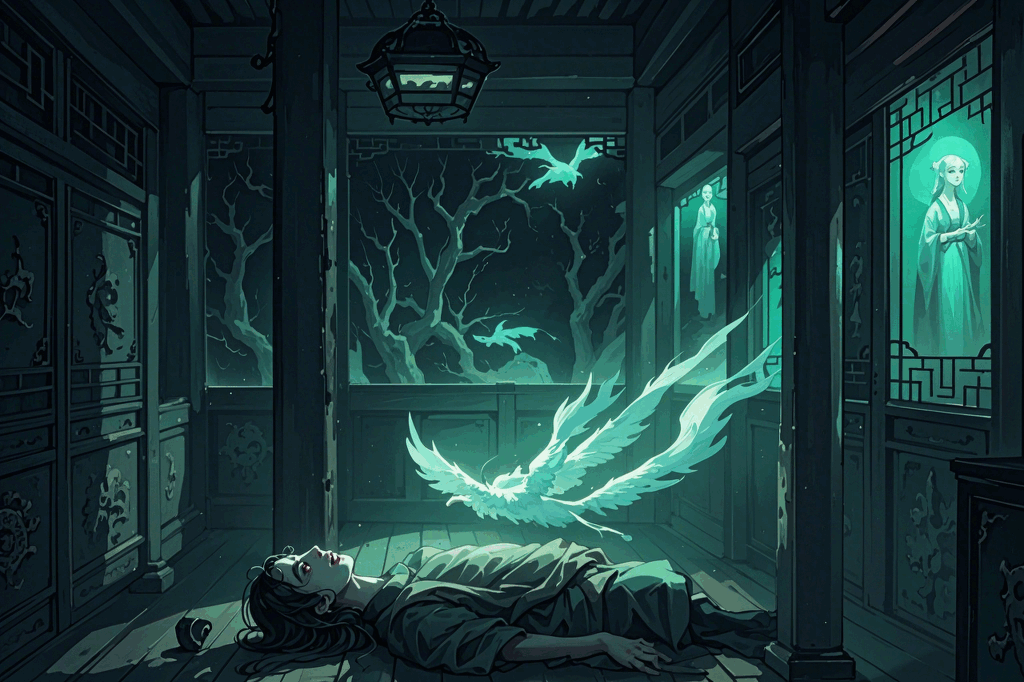时值我读小学时的某个暑假的某个晚上,天气闷热,四处无风。村中寨子的小孩子们在寨子外的大坪上玩耍,相互追逐嬉闹,有人还捕捉半空中闪烁的萤火虫,好不热闹。寨子内的大人们在露天处聊天,大部分房门都敞开着,房内的红色灯照射到屋外的地面上,屋外亮如白昼。大坪的右边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左边是呈阶梯状的村民的自留地菜园,菜园的上边是寨子的后山。
当时的小孩子中有一个叫小倩的女孩,为了追赶一只萤火虫跑进了菜园,忽然,她尖叫起来,声音尤其刺耳,其他正玩耍的小朋友立即停下来,跑过来问她怎么了。小倩一言不发,两眼发愣,指着菜园上边的后山。大家朝她指的方向望去,朦朦胧胧见到后山的矮小林木间出现一团红光,让人惊奇的是,这团红光竟然在飘动。
瞬间,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小朋友们都面带惊愕地望着后山,突然,后山上的那团红光消失了,在不远处又出现另一束红光,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束红光似乎朝人群飘来。
不知是哪个小孩突然大喊一声:“是鬼火,大家快跑!”小孩个个争先恐后地朝寨子的大门内跑。离后山最近的小倩也跟着别人跑,但由于紧张,跑到大门口时摔了个跟头,顿时嗷嗷大哭起来。此时,大坪上的所有小孩在瞬间跑得无影无踪。在寨子里的小倩妈妈—赖伯母奔跑过来把她提起,大发雷霆道:“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今晚不要到大坪玩,你偏偏要出来,看,摔倒了吧!”说完,赖伯母生气地抱起她,急急忙忙往大门口赶。
被母亲抱进大门口后,小倩惊异地发现,整个寨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原本喧闹的寨子在瞬间变得死气沉沉的,刚刚还一起玩的小孩子早已在大人的引领下匆忙回家,各户人家开始关门闭户。接着,各户人家原本开着的电灯也一盏盏地熄灭,刹那间,整个寨子漆黑一片。小倩被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放在床上。赖伯母关灯,叫小倩快点入睡。躺在床上的小倩却无法入睡,紧张而好奇的她在黑暗的睡屋中眨着眼睛。
大概过了一刻钟,窗户外呈现一片红光,接着传来一阵声音,似乎是位老者在呼唤,声音低沉而又拖沓:“曾——顺——你——回来——吧,曾——顺——你——回来——吧!”这声音在幽静的黑夜里显得非常清晰,并且由小变大。接着,这声音就停留在小倩家附近。当天晚上,邻居家动静不断,呼唤声、哭声、忙碌声夹杂其中,闹得通宵达旦,小倩在混混沌沌中渐渐入睡。其实,当时少不更事的小倩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当时在另外一个寨子住的我—小倩的同学,却少年老成,知道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农村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叫“招魂”。
招魂?即使传统中的招魂,也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让整个寨子的人为其避让呀。看来,这次的招魂别出心裁,独创一格。为何如此独特?事情必须追根溯源,从头讲起。
那天晚上的招魂主角之一即吴伯母的媳妇曾萍,她是个体弱多病的人,据说,她在整个青年时代,都是身体羸弱,面黄肌瘦,有气无力。曾萍是我寨人家的女儿,她嫁到小倩的寨子。当时的农村,经过数代人的繁衍生息之后,不同寨子的同性的男女结成连理的情况屡见不鲜。
但我寨的曾萍与另一寨的曾正哥结婚后发生了很多怪异的事情,甚至最终以让人垂泪的悲剧收尾。有人说他们的悲剧是近亲结婚,殃及后代;也有人说,是曾正的祖辈做了很多缺德事,最终报应在这一代显现出来;更有人在私下传言,曾萍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她曾经在深圳打工时……
在我的孩提印象中,萍姐是个多愁善感、温柔体贴的大姐姐。萍姐是我的邻居,当我7岁时,那一年她应是17岁,跟随村里的大队人马奔赴深圳淘金。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是我村的一个大趋势,很多家庭的小孩初中毕业后,甚至初中没有毕业,就经过熟人介绍去深圳的喇叭厂、电子厂、珠子厂打工。这些打工者在过年回家时,精神焕发地出现在农村留守者的面前,行李丰富,衣服光鲜,让人好不羡慕。当时邻居家一个哥哥回来后,我就曾在他的家门口守了半个多小时,仅仅是为了吃一块饼干。
可是,深圳打工者为家庭带来了较为可观的收入的同时,也可能有不为人知的辛酸的一面。据说萍姐每月把在深圳打工挣来的钱如数寄回了家,她的家庭也慢慢地富裕起来。
大概是萍姐出外打工两年后的某天,一个电话打到了村支书(他家才有电话)的家中,据说是村中外出打工的领头者从深圳打长途电话回来的,说是十万火急,叫萍姐的爸爸贵伯必须在第二天去深圳接女儿回来,但对于具体原因,打工的领头者却在电话中言辞闪烁。
贵伯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之中,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不幸这个鬼东西不请自来。当时他的预测有二:一是自己女儿可能已经死了,要他出去带尸体回来,不然为何自己不回来?二是女儿在流水线上发生意外,被送入了医院,并且绝对是重伤,不然怎么会叫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千里迢迢(其实只有四百多千米)去深圳接人呢?
事实证明,贵伯的担心并非多余,只是当时的贵伯并不明白,在深圳这个大都市面前,充斥着无尽的诱惑,不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农村人可以想象的。令人欣慰的是,女儿仍然存活了下来,表面上完整无缺,可是那颗原本纯洁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从深圳回来后的萍姐脸色黯淡无光,本来只有19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她看起来略显成熟,并且,萍姐的脾气也似乎变得有些难以捉摸,本来如花似玉的年纪应有的自信也已经荡然无存。她整天忧心忡忡、沉默寡言。有人闲言碎语地传言,萍姐是失恋造成的,难道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失恋真的如此让人害怕吗?未必,这事情肯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时间又过了一年,在家休养的萍姐收到了一封信(那时候流行写信),据说信封上邮戳盖的地址是深圳,萍姐读完这封信后,竟然一反常态,刹那间精神焕发。之后,萍姐向贵伯提出,不习惯农村的生活,要继续去深圳打工。听了萍姐的话,贵伯陷入了沉默之中,萍姐再次哀求,说她这次去深圳打工,并不会像以前一样无知,只会一心一意地想着挣钱补贴家用。
面对女儿的央求,贵伯始终沉默不语,而在一旁的贵伯母却一本正经地说:“阿萍,还想出深圳打工,你难道还不死心吗?你也20多岁了,我看你还是找个村里的普通男人嫁了吧。”
贵伯母的话可让人听不懂了,叫女儿嫁个普通男人,这是为人父母的愿望吗?谁不希望女儿嫁个仪表不凡、勤劳肯干的好男人呀?这可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幸福的事情,怎么可以随便找个普通男人嫁了呢?从中可见,贵伯母对阿萍未来的婚姻是没有什么奢求的。
果然,胳膊扭不过大腿,20世纪80年代的青少年虽说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爱情观念,但是父母的意见还是起主导作用。当时,萍姐在父母面前作出了最后的抗争,但她也彻底惹怒了贵伯。据说,当时的贵伯发火大骂时,寨子中有不少邻居听到。贵伯雷霆大发,声色俱厉地吼道:“你如果再出外打工,我就打断你的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现在嫁人的话,如果有人愿意娶你就阿弥陀佛了!”
在旁观者听来,贵伯的话有点耸人听闻,其实贵伯大动肝火,表明老一辈人对待爱情和婚姻的看法确实跟年轻一辈大相径庭。在高高在上的父母威严下,萍姐终于学会了农村妇女必须学会的第一点—逆来顺受。同时,贵伯犯下了第二宗罪,而第一宗罪则另有其人。
后来,萍姐在热心人的介绍下,嫁给了小倩寨子的曾正哥,曾正哥比她大12岁。但当时作为大龄青年的曾正哥并不检讨自己为何年纪这么大还没有娶老婆,却说萍姐为何这么年轻就嫁人。看来曾正哥跟萍姐结婚时也是心如明镜似的,彼此都认为对方不是什么好鸟。这正是:有些话可以心里想,却不可以嘴巴上说出来。
新婚两个月之后,萍姐怀孕的消息传出,这为曾正哥这个原本死气沉沉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但是,痛苦和悲伤也在这个家庭中慢慢开始生根发芽。
幸福的家庭生活只持续了3个多月,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早上,萍姐去河边洗衣服。(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农村妇女成为准妈妈后,就什么都不用干了,可以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当时,不要说洗衣服这类轻活,甚至下田插秧、上山砍柴都是可能的。)萍姐提着一桶衣服从寨中走了出去,沿着寨子外面的田埂走。当时正值春季,到处雾气弥漫,能见度很低,走着走着,突然,萍姐看到前面的田埂边有一个非常矮小的小孩,萍姐觉得非常奇怪,大清早的,谁家的小孩也不可能这么早起床呀!她回头看看是否有大人,但整片稻田中空无一人,她又往前走了几步,看到小孩浑身肮脏不堪,下身毫无遮掩,像是个小男孩。小男孩望着萍姐,露出乞求的眼神。萍姐在刹那间觉得小孩子非常可怜,料想小孩不小心摔倒在路边,需要帮助,于是萍姐走上前,伸手去拉小男孩。就在萍姐的手伸向小男孩的时候,小孩子也很配合地把手伸了过来,突然,小男孩用那忧郁的眼珠瞪了萍姐一下,同时用力一拉,萍姐大叫一声,失去平衡,倒在了田埂下。此时,她仍有意识,艰难地朝着旁边的小男孩看了看,发现小男孩慢慢站起来,光着稚嫩的脚丫,飘然而去。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小男孩飘走的瞬间,萍姐感觉心里就像被掏空了一样,生出生离死别的感觉,异常难受。小男孩消失后不久,萍姐突然感觉到下腹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她惨叫一声,昏了过去。
几分钟后,寨子中另一个要去河边洗衣服的妇女在半路上发现倒在田边的萍姐。她救起萍姐,把萍姐扶回家中。毫无疑问,萍姐流产了,但众人把萍姐的丈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说萍姐的丈夫让萍姐营养不良,贫血,还让萍姐在怀孕不稳定时期提那么重的衣服。当时,萍姐并没有把自己看到的怪异现象公之于世。
流产了,没关系,反正好好休养身体,以后再怀上就是了。流产现象在当时来说,比较普遍,所以不管是萍姐本人、其家婆吴伯母,还是其母亲贵伯母,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半年之后,在曾正哥白天忙农活,晚上忙人活的努力之下,萍姐再次怀孕,消息传出之后,家里都把萍姐当做重点保护对象,以免再次发生意外,不要说衣服不用洗了,连晚上出去大便都有双人陪护,家人可谓用心良苦。可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意外还是不期而至,但这一次,究竟是萍姐产生幻觉,还是邻居小孩作祟,几乎成为了我村的一大疑案!
一个傍晚,夜幕降临,刚刚吃饱饭的萍姐走出家门,来到天井处。此时,各户人家都在家里吃饭、洗澡什么的,灯光暗淡,四处无人。突然,一个邻居家叫阿伦的四五岁的小孩从寨子大厅中跑了出来,拿着一根棍子在比比画画。当时刚好六小龄童版本的《西游记》在热播,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小孩阿伦是受到电视剧的影响,在模仿孙悟空的动作。萍姐见到此景,也稍微后退,同时出于关心小孩,她多管闲事地说了一句:“阿伦呀,不要玩棍子,弄到自己的眼睛就不好了。”
阿伦立即停了下来,可是,他似乎生气了,竟然怒目圆睁地看着萍姐。萍姐不由得打了个激灵,因为在这瞬间她觉得阿伦的眼神似曾相识,她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突然,毫无人性的阿伦用他手中的“金箍棒”扫了过来,由于天色阴暗,萍姐根本毫无防备,金箍棒正中萍姐的肚子。萍姐顿时嗷嗷大叫,大喊起来:“抓住阿伦,抓住阿伦!”阿伦知道闯祸了,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寨子中几个人听到萍姐的叫喊都跑了出来,忙问怎么回事。正在家中吃饭的曾正哥也立即放下手中的碗筷,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然后按照萍姐的提示,疾步跑到上堂一侧的阿伦家找小孩家长理论。可是,争议就出现在这里,当曾正哥跑到阿伦家时,他一家5口人正坐在一张八仙桌前吃饭,阿伦父亲见到曾正出现在问口,问他吃过饭没有,还问外面怎么突然那么吵。
从阿伦的父亲在第一时间说出的这两句话分析,阿伦的父亲并非装腔作势,难道是萍姐看错了吗?这不得而知。萍姐因为遭受这次到最后也没有定论的一击,又流产了。当时,此事在寨子里闹得沸沸扬扬,萍姐家和阿伦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如果不是寨中人劝架,差点开打,但是最致命的一点是,除了萍姐,没有其他的证人,所以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两家人自此再也没有说话,虽说同住寨中,但形同陌路。
两次莫名其妙的流产让萍姐对怀孕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恐惧,但是事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一次像是贫血晕倒造成,一次像是小孩胡闹造成,但这不是关键的,因为还有第三次、第四次,每次都让人很揪心。
一年后,萍姐再度怀孕,并且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度过了十月怀胎期,终于等来了临产的那一刻。即将做父亲的曾正哥没有像今天在产房门口焦急等待的准父亲那样兴奋,他听到萍姐说肚子痛后,立即跑去村头叫来了接生婆陈婶。我相信,当时任何一个村寨的接生婆都是没有医师执照的,而我村至少有几个妇女有接生的经验,而村里公认为口碑良好、技术尚可的是陈婶,看来曾正哥叫来陈婶也算是明智之举。
陈婶趁着夜色来到曾正哥的家中,立即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工作之中。当时天气还比较热,一般农村人的睡床在夏天会挂着蚊帐,不然会被蚊子咬死。当时,萍姐已经进入生孩子的临界状态,疼痛得使劲号叫,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为方便工作,陈婶立即把蚊帐收了上去,正在此时,一个小东西,不知道是蚊子还是苍蝇,竟然飞了过来,钻进了在床上大喊大叫的萍姐张开的嘴巴里,顿时,引起了萍姐的恶心,她拼命地咳嗽着,想吐却吐不出来。
这难为了陈婶,因为萍姐翻来覆去让陈婶更难下手,还好,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忙碌,陈婶凭着她日积月累的经验,成功地完成了接生工作,一个婴儿从萍姐身体里出来了。据说,抱着婴儿的陈婶,一言不发,没有报喜也没有报忧,因为这个婴儿生下来就没有气息。躺在床上的萍姐脸色惨白,身子瘫软,或许,如果此时的她是清醒的,那么她应该是知道结果的,因为哪个孩子会生下来没有哭声呢?但她还是艰难地问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陈婶哽咽着回答:“是男孩,死了!”
面容冷峻的萍姐“啊”的一声,哭了,而在“啊”的瞬间,让人不可以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小东西从她嘴巴里飞了出来,然后在房间里转了转,从窗口飞了出去。此时,萍姐竟然悲伤地呼喊道:“宝宝,你别走。”她望向窗口,有气无力的手也微微向小东西召唤,这让在旁的陈婶看得浑身发抖。
准父亲曾正哥跑进了房间,知道竟然是个死胎,真是欲哭无泪啊!躺在床上的萍姐一直在叫喊:“宝宝,你别走,宝宝,你别走……”
当天晚上,乘着夜深人静,曾正哥拿来了一个簸箕,把死胎放在簸箕里,扛了一把锄头,挑着簸箕,来到后面的一个山坡上,把死婴埋了。
到此,村人都感叹萍姐不同寻常的遭遇和坎坷不平的命运,但是,婆婆吴伯婆并没有屈服,她还是想方设法补救儿子和媳妇的无子命运。她到主管传宗接代的观音菩萨的村尾庙宇去进行了一次虔诚的祈福,并且在菩萨面前许愿:如果生下小孩,把小孩卖给观音菩萨带,带到18岁,如果年底添丁,将拿以下东西酬谢:锦旗两面、鼓一只、锣三面。为何能把酬谢的东西记得如此清楚?因为确实是年底添丁,并且吴伯母也确实拿了这些东西到观音菩萨庙宇酬谢,而这些东西至今还保存在庙宇那里。
许愿的几个月后,萍姐又怀孕了,具体是第几次怀孕,她自己可能也搞不清楚,不过这却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怀孕。在神灵的保护下,同时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下,萍姐的肚子慢慢大起来了,最后两个月,她特地去县城的姑妈家安胎,最终在县人民医院生下了个小男孩,母子平安,小孩后来起名为曾顺。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多年后的今天,我村根本没有叫曾顺的人。
当时的曾顺,在一岁之内,算是平安度过,但是满周岁之后,大人们逐渐担心起来,总感觉他体弱多病,不是发烧就是头痛,这个可能跟父母的体质有关,因为萍姐在多次怀孕后,体质虚弱,多少还是有点遗传的。结果还是吴伯母老人家比较有办法,经常上山采草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但是,让所有人都觉得怪异的是,到了两岁,曾顺还不会叫爸爸。很多人会说,小孩子学说话时,根据小孩的声带发育,念出“妈妈”两个字比较容易,而念出“爸爸”两个字比较难,这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据说要曾顺叫爸爸时,他总是怪异地望着爸爸,好像爸爸是陌生人似的,如果强迫他叫,小孩就哭闹起来,坐立不安。或许这并不重要,因为再大一点,曾顺总会叫爸爸的,但是曾正哥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后山的那次丢魂事件,可以说是终止了一切。
小孩已经两岁多了。夏天的天气有点燥热,所以村民上山下田作业一般选择上午。那天,曾正哥和萍姐夫妻俩早早到后山的自家山上捡柴,萍姐是背着小孩去的。后山虽然坟墓和风水较少,但是参天大树多,枝繁叶茂的大树笼罩着整座大山,即使是炎热的夏天,来到此地都觉得凉风习习,舒适无比。
刚开始作业时,小孩一直在萍姐的后背上嘀咕,过了一会儿,小孩估计困了,逐渐安静下来,萍姐喊曾正哥过来看看小孩是否睡着了,曾正哥果然发现小孩闭上了眼睛。萍姐把缠在背上的绑带松开,然后把小孩放了下来,放在地上之前,她把绑带张开,让绑带像一张草席一样铺在旁边的平地上,再把曾顺轻轻地放在绑带上面,最后,萍姐在小孩身上盖了一件衣服。萍姐在曾顺的旁边捆柴,曾正哥则跑到另一边去了。突然,天空中的阳光被乌云遮蔽,瞬间山间阴暗起来,一阵阴风吹过,竟然把小孩身上盖的衣服吹走,萍姐立即去捡衣服,然后走了回来。
就在此刻,本来酣睡的曾顺,突然眼睛一瞪,眼珠子中白多黑少,一言不发,慢慢地爬了起来,曾顺随即打了个寒战,尿从裤子中流了出来。
萍姐吓得胆战心惊,急忙呼喊:“宝贝,你怎么了?”怪异的是,小孩子始终不理他,萍姐立即上去把他抱了起来,然后向曾正哥大喊道:“阿正,你下来,不知道宝宝怎么了,好像受到了惊吓!”
曾正哥听到了萍姐的呼喊,一路上披荆斩棘,从山上疯狂地跑了下来,焦急地问:“阿萍,怎么了?怎么了?”曾正哥看到儿子曾顺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个方向,突然,曾顺艰难地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堆草丛,吐字不清地说了两个词:“哥哥,哥哥!”
曾正哥迟疑了一会儿,突然脸色惨白,大喊道:“走,走,不好了!”他夺过小孩,拉着萍姐,疯狂地往家跑。回到家之后,曾正哥告诉萍姐,之前那个死胎就被他埋在后山,埋的地方正是小孩指的那堆草丛中。萍姐听了胆战心惊,同时也让她悲从中来,因为曾顺口中的哥哥也是她的小孩。曾顺这样说确实让人觉得非常诡异。毫无疑问,曾顺看到鬼了,同时他也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回到家之后,曾顺彻底病倒了。
吴伯母分析,孙子只是受到惊吓,叫儿子媳妇别担心,这不过是常见的丢魂。于是,他们当天提前通知了寨子中的各户人家,因为平时的曾顺本来就怕生,所以晚上请大家迁就一下,招魂时尽量避让,让她孙子的魂魄尽快重附其身,招魂仪式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举行,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当天晚上,为了曾顺的健康成长,家人已被搞得筋疲力尽,夜不能寐。但是从招魂之后的迹象来看,似乎效果并不明显。当时也请了神棍曾开,进行了一次作法,情况有所好转,一周之后,让大人感到欣慰的是,小孩竟然活蹦乱跳起来,后来确认这是回光返照。家人认为好起来了,就没有太留心,而小孩却在不留意间掉入了屋檐之下、天井之上的臭水沟中,面目朝下,引起窒息。当萍姐发现之后,她立刻把曾顺抱起来,曾顺污头垢面,嘴巴里都是淤泥。令萍姐想不明白的是,小孩只剩下最后一丝气息,竟然喊了一句“哥哥”,然后离开人世。
小孩死了,萍姐的家庭随即破裂,吴伯母原本健朗的身体渐渐垮了,曾正哥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万念俱灰的萍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落得这样的结果,还好,她没有想不开,而是坚强地活了下来。据说,她在一个深夜里留下了一封信,离开了我村。从此,我村的人再也没有见到她。
大概一年后,我村有一人在梅州市的一座名山上的寺庙中烧香拜佛时,见到了一个长得非常像萍姐的尼姑。萍姐的父亲贵伯听到这个消息后,却不以为意,认为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由她去吧。
过了3年,贵伯家收到一封从广东湛江寄过来的信,收信人是曾萍。贵伯打开信,读完之后老两口已是老泪纵横。此信为湛江的一个男人所写,信的内容大概是,说他在深圳跟萍姐分手之后,回家娶了老婆,但是自己的生活却一直过得不顺利。一次,自己由于好心去救一位掉入石灰水中的小孩而造成双腿烧伤截肢。让周围人大为诧异的是,当时根本没有小孩掉进去,所以当地人都认为他是疯子,他的这种行为是自残。他也觉得莫名其妙,无法找到根源。后来,他的父母请来一个法术高明的大师,作法中竟然说他曾经屠杀生命,在他身边,一直有个婴灵左右他,所以有如此后果。他立即想到,大师说到的这个婴灵肯定是自己当年在深圳时让萍姐怀上而又被打掉的小孩。现在已是残疾的他整天诵经念佛,超度亡灵。他想知道这几年萍姐的情况,如果有婴灵报复的迹象,希望她同样诚心超度亡灵,赎回当初的过错。
可惜的是,萍姐永远也看不到这封信了。但是,她提前遁入空门,或许,这就是上天对她的最佳安排。
看来,胎儿本来就是生命,女人堕胎,男人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