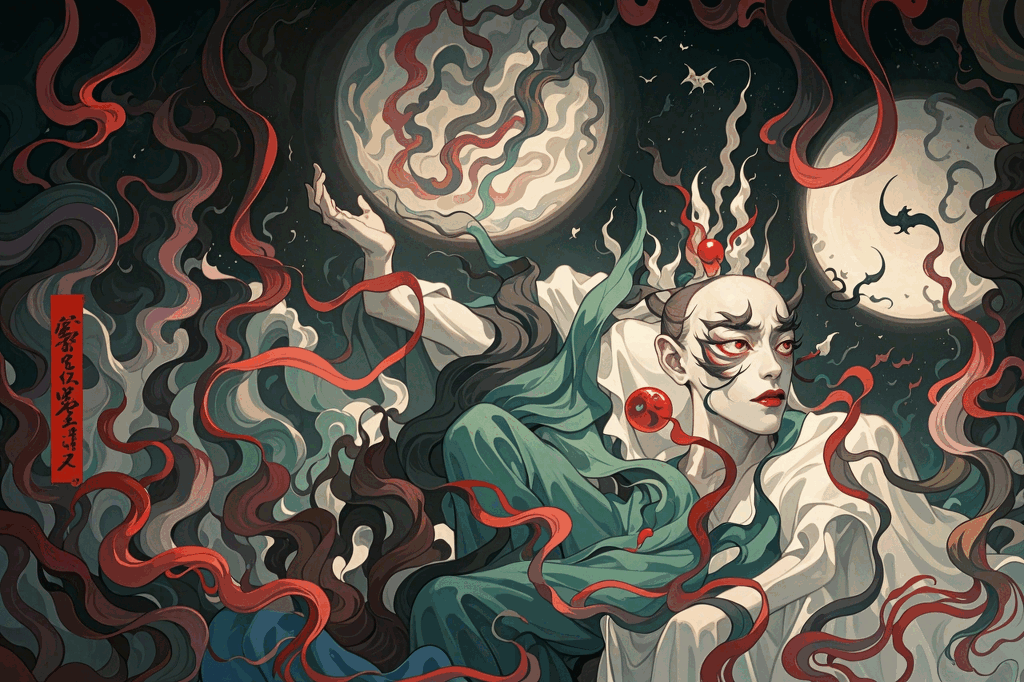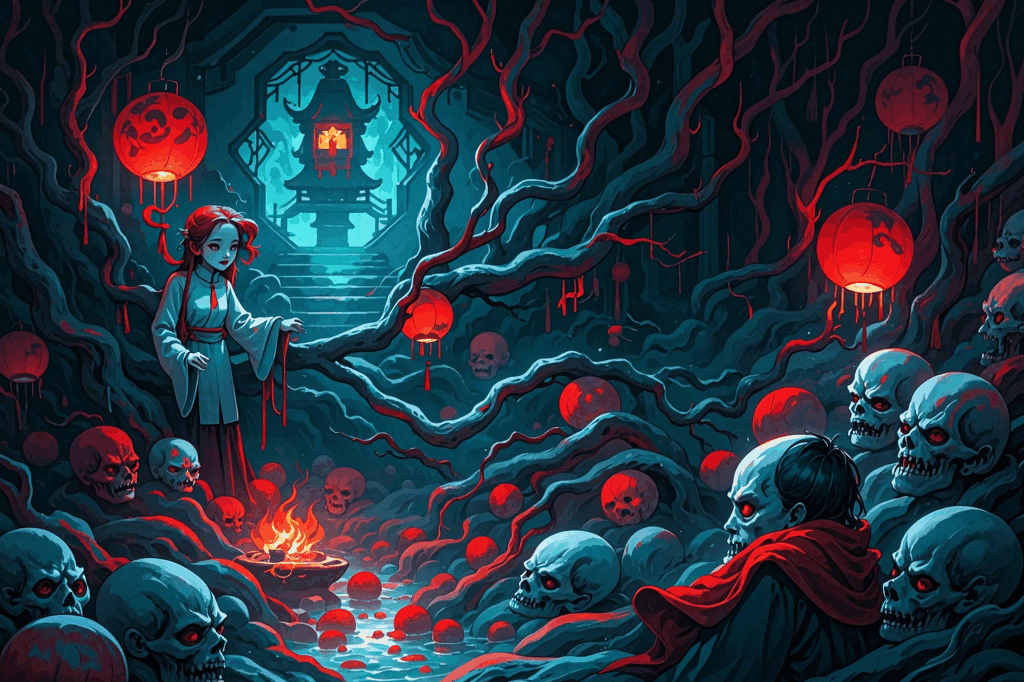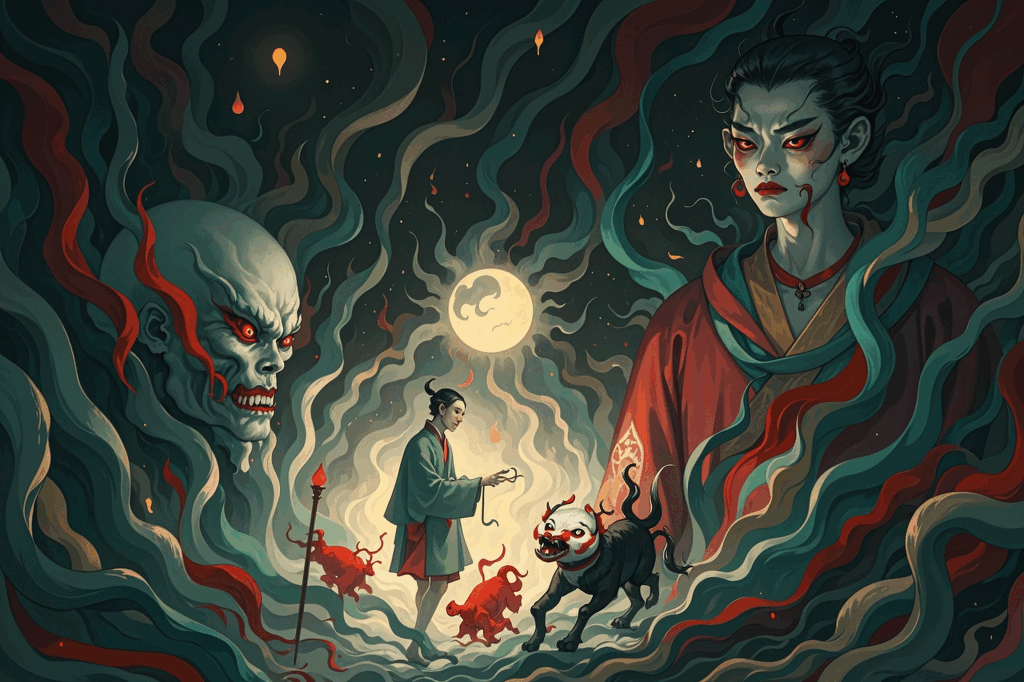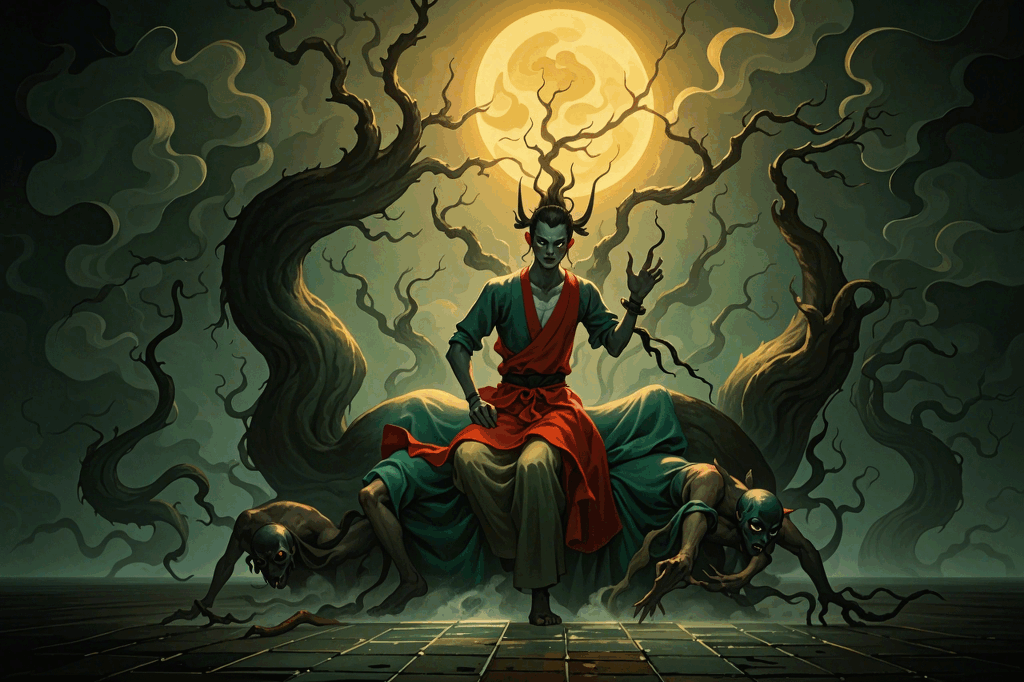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某个夏天的某个晚上,时间逼近午夜零点,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已经熟睡,而我睡房的隔壁—运哥房间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并且有人喊道:“喂,开门!”声音停歇了一会儿,接着又传来了踢门声,踢门声从斯文到粗鲁再到狂野,但房间里面似乎仍没有反应,最后,传来女人咆哮的声音:“运哥,你快开门,再不开我就劈门了!”此时,在隔壁房间侧耳倾听的我果然听到了金属的响声,料想这个女人说话一点不假,确实是带了劈门的工具,这让人在这黑夜里听了胆战心惊。
然而,不管外面有多大的动静,运哥的房间里仍是寂静无声,左邻右舍的几个房门陆续地打开了,此时,我也打开房门从门缝口向外张望。寨子中有几个人穿着睡衣走了过来,其中有一个人一边扣衣服的纽扣,一边怒气冲冲地喊道:“陈嫂,你在干什么?三更半夜劈人家的房门干什么啊?”
说话的叫盘伯,他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应该是刚刚被吵醒。他就是陈嫂口中的“运哥”的父亲。盘伯一脸严肃地到陈嫂的旁边,猛地把陈嫂手中的刀夺了过去,嗔怒地对陈嫂说道:“你是找你老公吧?怎么找到我们家来了?还有,你拿着刀干什么?你想杀人啊?”
被盘伯的话当头一击,陈嫂顿时哑口无言,她犹豫片刻,才慢吞吞地说道:“昨天下午是运哥找我老公泥头的,运哥找我老公,会有什么好事?除了去赌博还会去做什么?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昨晚一个通宵,我可以不管,但今天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这还了得呀?”
盘伯和众人听了陈嫂的话,颇觉有理。盘伯柔声细语地对陈嫂说道:“这个赌博是泥头不对,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拿刀劈门吧?我家运古也是已经两天晚上没回家吃饭呢,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你踢门之前也不看看,真的有人在房间里面吗?”
陈嫂愣住了,她从门缝里看到房间里面根本没有光,才知道自己是白忙活一场。盘伯见陈嫂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鲁莽,便心平气和地对陈嫂说道:“你也知道,最近村子里的赌博泛滥,几次被人举报,连镇里的派出所都出动了一次,我看他们肯定是藏在村尾寨子那些比较隐蔽的地方了。哦,对,你问问管婶,她肯定知道。”盘伯指着正走过来的管婶说。
没错,管婶的丈夫管叔也是一个专业赌徒,只要村里开赌,他必参战,并且,对于管叔赌博一事,管婶从不干涉,因此,在管婶面前,管叔对自己的赌博行踪一直直言不讳。管婶大老远就听到了盘伯的话,她走过来说:“我那枪决鬼还不是整天日赌夜赌,他前天出去赌了,中午才回到家呢,回来便倒在床上睡觉,睡到现在也还没有醒来。”
陈嫂听了,更是心头一惊,管叔都回来了,泥头怎么还没有回来呢?难道赌博一直没有停过?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这对于赌徒来说,也情有可原,因为赌徒的心理就是,输了想赢回来,赢了想赢多点,一直赌下去。
盘伯也有点糊涂了,因为他儿子运哥也没有回来,于是他问管婶:“这次他们这些人在哪里开赌呀?怎么赌了这么久?”
管婶心直口快地说道:“筒子冈!”
现场所有的人听了都呆若木鸡,陈嫂更是大声“啊”了一声,惊讶得合不拢嘴。筒子冈是什么地方?不是一个寨子的名字,也不是一户人家的名字,而是一座山名,最要命的是,这座山跟百叶岗一样,是我村村民无比熟悉的一个鬼地。我村的赌徒们竟然聚在鬼地赌博,说出来实在是惊世骇俗啊!
要了解这种特有的现象,必须简单地介绍一下我村的赌博发展历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村的赌博道具绝不是今天通用的麻将,而是扑克。众所周知,扑克的玩法花样百出,但我村赌徒玩的只有一种,客家话叫“pia”,而英文的说法是“show hand”,就是5张牌的那种,第一张底牌,其他4张明牌,在每发一张牌时按照大牌轮流下钱,最后开牌。在当时,通货膨胀并不厉害,但如果打这种牌,普通一场的赌注可以达到四五百元,赌注大的,更是可以上千,所以非常刺激,让无数的赌徒趋之若鹜;并且,我村的赌徒较多,声势浩大,造成我村的赌博现象在我县都比较出名,很多其他村子的赌徒经常来我村赌博,后来,连五华县一些乡镇的人也会来到我村参赌。或许赌博是我村村民的天性,即使是现在,搬离到别处定居的我村村民,偶尔在他乡见面,也是以赌博作为招待节目,名曰“聚会”或“娱乐”,其实本质是赌博,因为不玩钱,谁会去玩呢?同样,我也不例外,我对各地区的麻将玩法都了如指掌。
当时,我村因赌博的人多了而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影响较大,必然受到政府的打击,这势必影响到赌徒们,所以他们把赌场选在隐秘的地方,如村尾寨子或者人家的棚上等;二是因为赌资大,必然要“抽水”,一般由所在的屋主“抽水”,每一场抽5元、10元,叫做“电灯费”、“水费”或者“服务费”,毫无疑问,这种“抽水”费用非常高,往往一个晚上可以达到成百上千,所以赌徒们的压力很大,有时一个晚上下来,大家都没有赢钱,提供赌场的房主却赚了个盆满钵满。于是,在赌博过程中为了避免遇到上述两个问题,大家逐渐地向牛栏、野外等地方聚集,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赌徒竟然发展到鬼地筒子冈去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呀!
按照时间推论,筒子冈的这次开战已经持续一日两夜了,难道还有部分赌徒不愿散去,仍在苦苦奋战吗?看来身边知道内情的人,只有管婶的丈夫管叔了。管婶也是个热心人,带着陈嫂和其他几位邻居深更半夜来到她家。
管婶悄悄地来到房间,叫醒了仍在熟睡中的管叔。管叔被突然惊醒,大叫道:“还差一张牌呢,肯定是我大,哎,怎么醒来了!”管叔显然是个嗜赌如命的人,连梦中都在赌呢。可是,管婶却不让他继续做春秋大梦,管婶拉开了电灯,寨子里的几个人黑压压地站在他的面前。管叔揉了揉眼睛,他首先看见了陈嫂,毫无顾忌地对陈嫂说道:“你老公厉害呀……”刚说了一句,管叔发现自己说漏嘴了,因为这是赌徒忌讳,在赌场外不谈输赢。最重要的是,泥头不比管叔,泥头的老婆跟自己的老婆不一样,泥头的老婆陈嫂可是管着泥头的,所以泥头赢输多少,千万不能在陈嫂面前提起。
但管叔说一半留一半,这却让陈嫂不乐意了,她迫不及待地问管叔:“管叔,你刚才说泥头怎么厉害了?”
管叔望了望陈嫂,又看着其他几位在场的人,仍然没有张口,旁边的管婶说话了:“你就说吧,泥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呢,他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管叔听了管婶的话,脸上立即露出了一丝疑惑不解的表情,但他的这种表情,实在让人弄不明白他究竟是没有睡醒还是故作糊涂。此时的陈嫂终于按捺不住了,焦急地问道:“管叔,你离开时是不是还有些人在筒子冈开赌呀?”
管叔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说道:“确实是,我上午回来时,还有一部分人刚去呢,肯定今晚又是个通宵。你说泥头没回来,这不可能吧?他是跟我一起回来的呀,难道到现在他都还没有到家吗?这也太奇怪了,他不会跑到别人家去睡觉吧?”
此时,不仅是陈嫂觉得奇怪,连一旁的盘伯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他喃喃自语道:“按理来说,泥头不比我家运古,如果是年轻人,去别人家过夜还说得过去,泥头可是有家室的人,赌博再晚回来也应该回自己家呀。会不会是陈嫂你管得太严了,他回家怕挨你骂呀,你看你,刚才还喊打喊杀的呢。”
陈嫂变得愁眉不展,摇了摇头,说道:“虽说我每次都会说他赌博这事,但说完了他照样我行我素,我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会不会是他这次输得很惨,不敢回家呀?”说完,陈嫂焦急地望着管叔。
管叔挥了挥手,连忙说道:“不会,不会,你还别说,泥头啊,他昨晚的运气可好了,到最后跟我一起走时赢了两千多元,怎么会输?刚开始时他输掉两千多元呢,没想到下半夜他竟然反败为胜,真是难得。”
赌徒管叔说得头头是道,陈嫂现在对赢输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她只想知道泥头的下落。可是,管叔也一脸茫然,突然,他面带惧色地说道:“惨,惨,惨,泥头肯定是被鬼迷住了,真的,他昨天晚上很怪异呢,上午跟我一起回来时,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管叔思索了一会儿,接着说:“真的,现在想起来,肯定是,他昨晚的表现真的有点怪异。”
什么,被鬼迷住了?众人听了个个目瞪口呆,尤其是在这子夜,谈起有鬼,更是让人惶恐不安。众人不由自主地向房间中心靠拢,认真地听管叔讲述那惊人的一幕。
昨天下午4点,第一批赌徒向鬼地筒子冈进发,赌徒成员有:管叔、泥头、运哥、风古等9人,后勤成员是察鳖两公婆,主要负责道具,比如扑克(多副备用)、蓄电池、面包、饮料、草席、账本等。因为阵容强大,并且赌博开场前的兴奋已经取代了平时对鬼地的恐惧,所以他们来到鬼地时谈笑风生。察鳖两公婆其实在来之前已经物色好了半山腰上的一块草地,此处地势低,周围林木耸立,让赌徒有安全感,并且,此处远离村庄的喧嚣,不会出现只看不赌的看客。这类看客在赌博过程中会唧唧喳喳从而影响赌客的赌兴。
刚到目的地,察鳖迅速在草地上摊好了几张草席,赌徒们盘膝而坐,在草地上围成一圈,迫不及待地准备开战。大家都抽出一沓人民币,开始下头10元,然后发牌,打钱,发牌,打钱……第一场管叔赢钱,他在抓起草席上的钱的同时,拿出一包烟,一人派发一根。
但是,第一场赢钱的并不一定可以坚持到最后,因为第一场之后,后面是无数次的考验。果然不久之后,管叔的赌运急转直下,几次看似赢定,却被村中赌王风古吃掉。奇怪的是,坐在他旁边的泥头也是输多赢少。两眼发红的泥头好像已经不停地从不同口袋中掏钱出来,这意味着泥头在天黑之前,已经输得差不多了。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到了傍晚7点,天色逐渐变暗,察鳖在人群两边各打入两个木桩,然后把两个灯泡挂上,打开蓄电池,草地周围亮如白昼。
此时,场中的各位赌徒均有小胜小负,泥头至今还没有开始赢钱。天黑之后,泥头更是输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或许因为自己输得厉害,造成心虚,几次比较大的底牌,只发到第三或者第四张,就不敢跟了,造成了很多的遗憾。其实,这也不怪他,因为泥头跟其他赌徒不太相同,那就是泥头的钱基本上是血汗钱,输多了难免泄气,这是这一类型赌博的大忌。因为这种赌博,良好的心理素质非常关键,如果心虚,让财大气粗的人吓唬是很有可能的。管叔还好,在天黑之后赢了几场大单,他为人豪爽,见旁边的泥头输光了带来的本钱,立即借给他500元,让他翻本。
可是,原本搏一搏,想着单车变摩托的泥头,刚借的500元又很快输得分文不剩。赌王风古见他如此,颇有良心地说道:“泥头,我看你今晚也挺背的,先休息几场,转转运再来。”
泥头额头冒汗,脸色苍白,于是他暂时终止了发牌,然后就地站了起来,伸伸懒腰,自嘲道:“他妈的,一个晚上没赢几场,也不知道是不是给尿憋的,走,去尿尿。”他独自一人闪进了旁边的林子。
据后来得知,此时的泥头仍然保持着必胜的斗志,他头脑清醒,走到一个偏僻处撒尿。小便完后,果然感到十分轻松,他后悔不迭:早就该来透透气了。这很有道理,自古以来赌博之人,遇到势头不好,有的去撒尿,有的去喝水,有的要求换位,有的要求换牌,有的要求切牌,甚至有人跑到厕所去换内裤,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变之前发牌的概率,从而造成牌势的逆转。泥头看着周围阴森森的林木,没有感到丝毫的害怕,因为今天晚上的主题是赢钱。他抽了根烟,大脑中呈现着刚才的牌势,他踱来踱去,走到了不远处的岔路口,在暗淡的灯光下,竟然见到了一穴风水。
泥头突发奇想,毫不犹豫地走到风水面前,靠近碑石,擦着了火柴,在模糊中见到了碑石上的字,大概是“祖考曾公维宁之墓”。泥头退后,跪在风水面前,念道:“维宁公呀,你要保佑我今晚赢大钱呀,赢钱之后,我会好好地酬谢你哦!”然后拜了几下。在这漆黑的夜里,泥头的动作有点滑稽,虽然泥头知道碑石上的名字大概是我村谁的父亲,但是他全然不知道,这位死者曾经是我村鼎鼎大名的“赌鬼”。
泥头“自我放松”之后不久,又回到了赌场,此时的他心潮澎湃,意气风发,他又向管叔借了200元做本,继续参战。让其他赌徒大开眼界的是,奇迹出现了,第一场竟然是泥头赢钱,泥头心里乐滋滋的,他兴奋地从席上抓钱,他相信,自己赢钱一定是不远处的那位先人在黑暗中保佑着自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二场泥头竟然以底牌最大取胜,让其他赌徒叹为观止。第三场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或许是因为泥头的气势压倒众人,泥头竟然以吓唬取胜赢钱。见泥头撒了一泡尿回来之后变得势不可当,其他几个赌徒也提出要去撒尿,此时赌博只能暂停。据说三场赢钱,泥头已经翻本一大半,此时的他一边整理着纸币,一边心中感谢着那位先人。
众人再次回来之后,发牌继续,果然牌势又被打乱,第一场并不是泥头取胜。但是,在之后的决战中,泥头牌势总体还算可以,输少赢多。时间不知不觉进入子夜,草丛周围时不时发出奇怪的叫声,尽管挂着的灯泡招惹了不少虫子,凉风习习却让人备感舒适。但赌徒无暇顾及这一切,个个都是睁大那熬红的眼睛,盯着草席上的扑克牌与纸币。
据说,关键的一场牌到来了。此场牌跟到第四张的人尤其多,所以席上的钱也特别多,有800多元。最后一张牌发下来,其他跟牌的人个个收牌不跟,因为赌王风古的牌已经是明牌3个“6”,其他人不可能大过他,唯一跟的是泥头。泥头在后来讲,当时他是没有看底牌的,因为他的4张明牌已是同一黑桃颜色,只要他的底牌是黑桃,那他就赢定了。
现场的气氛非常紧张,个个盯着泥头的一举一动。管叔看到泥头向对面的空隙处瞥了一眼,然后像是得到谁的肯定似的,竟然下钱跟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还大了风古50元(首尾50,大3轮),风古一脸愕然地看着泥头,不过他还是扔钱开牌。
泥头却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他没有揭开自己的底牌就去席上抓钱,风古原以为泥头已经看牌了,也以为是泥头赢,于是随手翻开了泥头的底牌,竟然是红桃3。此时,不仅仅是风古,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风古立即抓住了泥头的手,大声说道:“泥头,你怎么搞的,去洗洗脸吧,你是红桃3呀,不是黑桃3呀,是不是灯光不够亮呀?”
泥头大叫一声,认真地看着底牌,没错,自己看得一清二楚,确实是自己搞错了,他不好意思地放下了钱,缩回了手,擦擦额头,说道:“不好意思,搞错了,搞错了。”然后回头朝着自己的后面喊了几句“他妈的”。或许连续开战的时间过久,造成了泥头的视觉疲劳,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更加诡异的事情还在后头。
泥头错失大单,颇受打击,他又去旁边的林子休息了。旁边的管叔见他一声不吭地朝林子走,看着泥头失落的背影,颇觉古怪,他疑惑地对众人说:“泥头不会有什么事吧?”
几人也朝泥头的背影看去,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其中有一人漫不经心地答道:“别管他了,他又去撒尿了。等下回来他又力压群雄了,我们还是趁着他离开尽快开战吧。”说完,众人又聚精会神地赌博。
泥头后来说,当时,他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去的,前面似乎有一个老人的身影引导他过去,他刚才大胆下注,也是因为看到了人群后面的黑暗处有一个人向他点头暗示。但是,他这样说确实有点牵强附会,更可能的是,他当时输得太多,受到了较大的打击,并且赌博很消耗体力,如果你将连续打10个小时麻将,到最后诈和可能都会搞出来,毕竟人的精力有个限度,你超过了这个限度,各种奇异的景象都可能在大脑中形成。而此时,更加巧合的是,时间到了深夜一两点钟,正是鬼地这块不祥之地各界生灵开始蠢蠢欲动的时间。
在微弱的光线下,泥头独自一人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那穴风水旁边,然而令他惊奇的是,左侧的土地上却热闹非凡,有三四个人围在那里赌博,哇,今晚真是壮观,开了两个赌场呀。泥头想走过去观战,却发现自己的脚步非常沉重,在他前面的那位老者站在墓地前转过身来,但老者面容竟然模糊不清,老人得意地对他说道:“你赢不少钱了吧?”
泥头根本没有去想眼前的这位老者是谁,或许他还以为是刚刚一同出来撒尿的赌友,他破口大骂道:“赢个屁,刚才一场都输了1000多元,他妈的。”他说完朝风水上吐了一口痰。
老人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安慰他说道:“人不能太贪心,适可而止,赌博输赢,乃运气左右,不可太强求!”
这老人确实说中了泥头的要害,据说此时的他也赢了不少,见兜里有不少人民币,他转怒为喜,拿出烟盒,点着了一根烟。
见泥头被点化,老人若有所思,他动作轻缓地指了指泥头的口袋,然后又指了指坐在土地上的那群赌徒,泥头立即会意,应该是这位老人要向自己借钱。但奇怪的是,他感觉自己的手感觉神奇,竟然情不自禁地从口袋中掏出了两张大团结,然后又缓缓地掏出火柴,把这两张人民币点着了,一簇弱小的火焰在空气中慢慢地晃动,人民币转眼间成为灰烬。
“泥头,你在干什么?点火抽烟吗?”突然,正在岔路口撒尿的管叔大声叫了起来,声音在这黑夜里显得非常响亮。泥头回过神来,惊讶地看着正在燃烧的人民币,立即扑灭,但两百元只剩下一个边角。此时,管叔已走到他的旁边,估计也看到了他手上残留的人民币,胆战心惊地问道:“他妈的,你不会有病吧?你在这里烧钱?”
泥头似乎意识到自己不正常,立即站了起来,看着两张只剩下边角的人民币,一脸后悔的样子,毕竟即使银行行长是自己的父亲也没用,也不可能给他兑换如此残缺的人民币了。据说,后来这两张人民币一直被他保存了下来,或许他这么做是为了纪念自己曾经拥有的非凡时刻,同时也是提醒自己远离赌博。
稍微清醒的泥头,跟着管叔战战兢兢地回到了赌场。山间的赌场仍是人声鼎沸,每个赌徒都全无睡意,赢的在欢呼,输的在叹气,他们在透支自己的生命,在享受着赌博带来的快感。泥头回来之后,又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赌博一直在继续,此时是夏日,夜晚非常短,5点多钟天就大亮了,而到8点钟,第二批赌徒已经来临,于是,犯困的人逐渐退出,而管叔和泥头又坚持了一会儿,大概10点,两人准备撤离。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征战”,何况这种“战斗”大起大落,时而兴奋,时而失落,精神绷得特紧,体力难免不支。还好,令人欣慰的是,赌徒泥头最后“战绩”不错,据说赢了两千多元,这不过只是暂时的,只要他以后还赌,永远是不能说赢的。
但无论如何,他算是对自己这次通宵达旦的“工作”有个好的交代,可是,精神的颓废,体力的透支,让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了。
当时泥头跟着管叔走,还好,前面的管叔是比较清醒的,后面的泥头从筒子冈走下坡路时就跌跌撞撞,差点摔倒,还是管叔几次回头大声喊住他,他才强打起精神,继续向下走。
泥头额头冒着冷汗,这很可能是熬夜并且少喝水而造成感冒的迹象,当他们勉强走到屋子附近的茅厕时,泥头说了句:“管叔,你先走一步。”然后就闪进了一间茅厕,像是在呕吐。管叔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到家了,自己也困得不行。他回到自己家,从厨房里找些剩饭剩菜囫囵吞枣地吃了,倒在床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一直睡到现在管婶叫他起来。
从管叔的讲述中,可以确定的是,泥头早已离开筒子冈,并且已经回到了寨子的附近,但寨子是弹丸之地,他能去哪里呢?当然人是活的,如是他倒在柴房、茅厕、后屋檐,都可能让人找上大半天。陈嫂早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搓手顿足。可是,急也没有用,这深更半夜的去哪里找人?你总不可能挨家挨户地敲门吧。
盘伯的话打破了屋子的宁静:“这个赌鬼,不会神志不清,掉进粪池里吧?”
盘伯的话绝不是开玩笑,农村的粪池,大而深,容积大,我村曾经就有小孩掉入粪池淹死的。不过,泥头是个大人,估计掉进去也淹不死吧。但结合泥头回家时已是晕头转向的情况,掉进粪池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事不宜迟,陈嫂跟其他几人立即拿了几根木棍,带了几支手电筒,向茅厕出发,挨个粪池搜寻,每搜寻一个粪池,就向里面捅了捅,结果,并没有发现一个粪池里面有坚硬的人形物体。
陈嫂惧怕了,呆呆地站在搜寻的最后一处粪池的旁边。此时,她宁愿相信泥头还在筒子冈赌博,也不愿意相信泥头已经回来,回来却不见踪影,怎么可能不急呢?
突然,在旁的盘伯眉头一皱,在黑夜里仍然可以看到他的目光很深邃,他问管叔:“阿管,你刚才说到泥头在山上时的异常,我认为那不是他的幻觉,他真的被鬼迷住了。你们在筒子冈赌博的地点,是否是在那两棵高大的自留杉树旁边的那块草地呀?泥头烧钱的那穴风水就在草地左上方的岔路口吗?”
管叔惊讶地答道:“对呀,就是那里!”
盘伯恍然大悟,像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肯定是在那里,肯定就是在那里,大家跟我走!”
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说话,都跟着盘伯走。盘伯绕过了这一排茅厕,然后走了一小段上坡路,来到一个牛栏前。哎哟,这不是已搬离我村的柱叔家的牛栏吗?有人立即想到,这屋以前不是牛栏,而是柱叔家的旧屋,后来柱叔家搬新屋之后,这里后面的几间倒塌了,而前面的一间做了牛栏。最让大家害怕的是,柱叔的父亲叫维宁叔公,就是那座坟墓的主人!
大家战战兢兢地站在牛栏门口,周围一片寂静。耳朵灵敏的陈嫂已经听到了里面打呼噜的声音,陈嫂喜上眉梢,她已经确定里面是泥头,十多年的同床共枕,泥头的呼噜声,她无比熟悉。她首先走了进去,手电筒在四周晃动一下,终于在墙角处看到了鼾声如雷的泥头。
陈嫂跑了过去,大声喊道:“泥头,泥头,你醒醒!”
外面的几个人听到了陈嫂的喊叫,也跟着进去,几把手电筒照在地上,却发现,周围到处是飘散着的钱,管婶随手捡起一张看看,立即发出一声“啊”的惨叫,甩掉了,然后躲在管叔的后面。看着地下花花绿绿的一大片钱,众人更加搞不懂这牛栏里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唯一可以解释的人是泥头,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墙角的泥头。
在陈嫂的摇动和呼喊下,泥头终于睁开了他那疲惫的双眼。众人发现,泥头的身上到处都是蚊子咬过的疤痕,在一个蚊子如此多的地方泥头竟然睡得如此沉,他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泥头刚刚睁开双眼,就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惊讶地说:“我的钱呢?”
盘伯晃动着手电筒,照了照地面,许多张钱呈现在他眼前,泥头放心了。
陈嫂一张张地收拾着地下的钱,等看清后,她惊呆了,大部分都是冥币,但中间也有人民币,两者混在一起,让她捡得哆哆嗦嗦。最后捡完,经统计,有三千多元人民币,据清醒后的泥头确认,数目分文不少。为何出现冥币,为何人民币和冥币混在一块,难道这一切都是赌“鬼”搞的鬼?
状态恢复后,泥头告诉了众人真相,而这个真相似乎经得起逻辑的推敲,所以可信度很高,当时的大部分村民对此事毫不怀疑。
泥头说他回家的时候身体确实疲惫得接近极限,双腿已经完全无力,刚走进茅厕就感到要晕倒,迷迷糊糊中,似乎有人扶着他来到了房间(牛栏),他倒在地上,实在是太想睡觉了。可是,蒙眬中,一位老者现身,说要跟他赌,提到赌,泥头哪有不参战的?于是他跟这位老者进行了对决,双方一直这样轮流出钱,非常刺激。
赌“鬼”毕竟是虚无缥缈的,冥币呢?那可是以实体存在的呀,后来有人考证,冥币根本不是维宁叔公从地府里带来的,而是老屋子里的一角堆放了很多废弃东西,其中的一个坏竹篮里放置了一沓沓的冥币和草纸呢。估计是以前柱叔家供祭祀用的,搬走时还没用完就扔在那边,而赌“鬼”就地取材……
让人相信赌“鬼”真实存在的是,我村很多年纪较大并且了解维宁叔公的人,说维宁叔公生前嗜赌如命,经常在各种场合中参战,据说,临死前的一个月,维宁叔公还跟一群老人在切磋技艺呢。看来生死虽不同路,但爱好还是相同的啊。
赌徒泥头自从跟赌“鬼”维宁叔公交手之后,似乎有戒赌的迹象。但我村村民的赌性依旧不改,或许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赌博,没有人能在开赌前知道结果是赢是输,但是,赌钱,还是少沾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