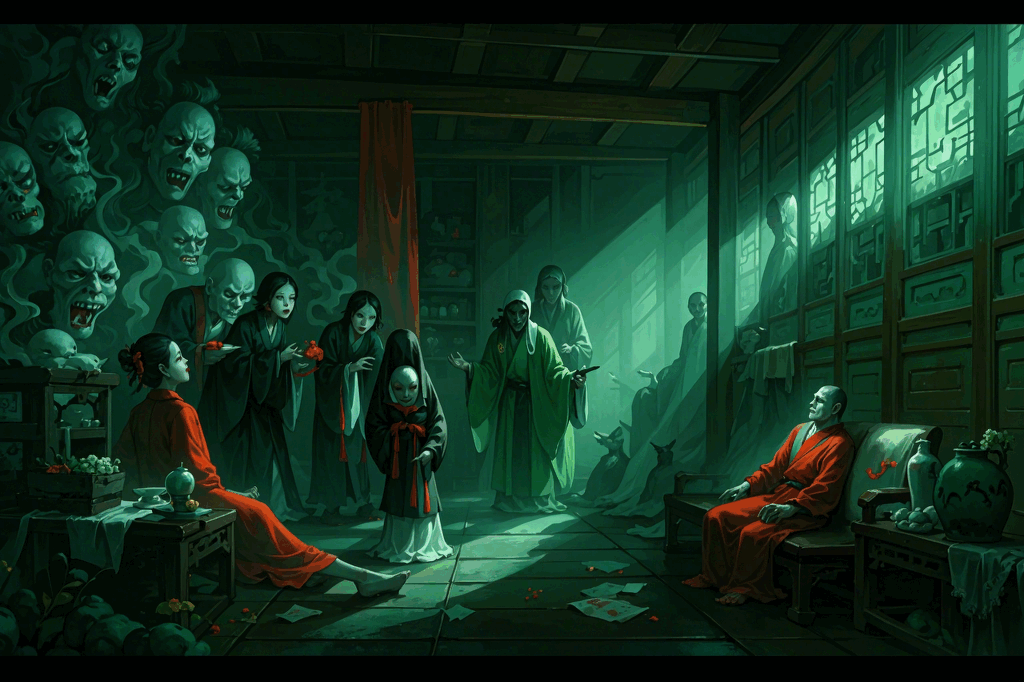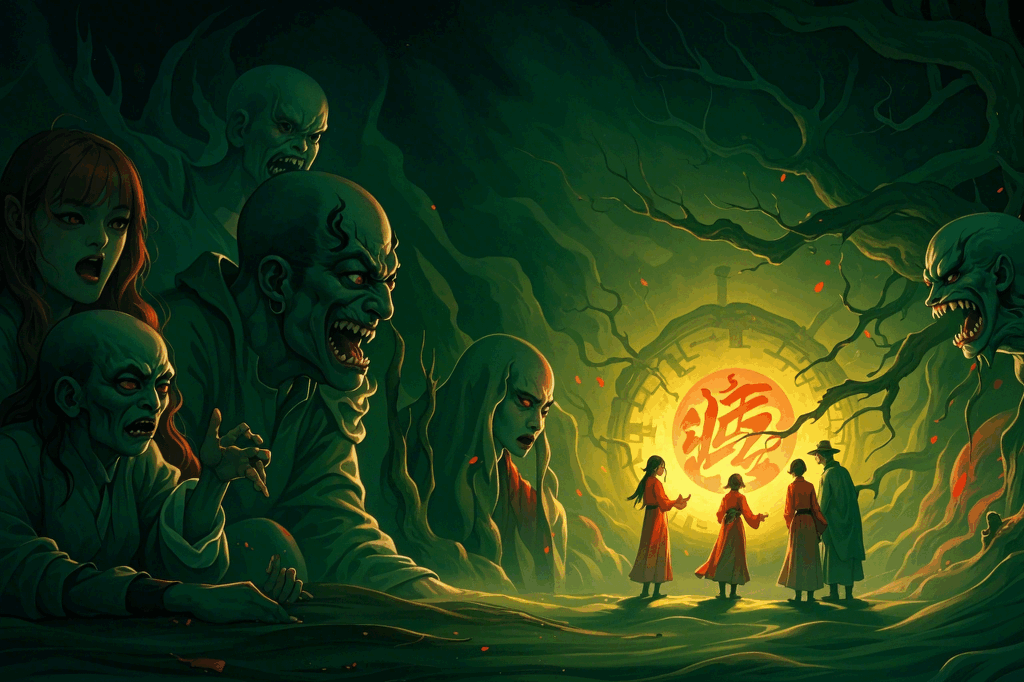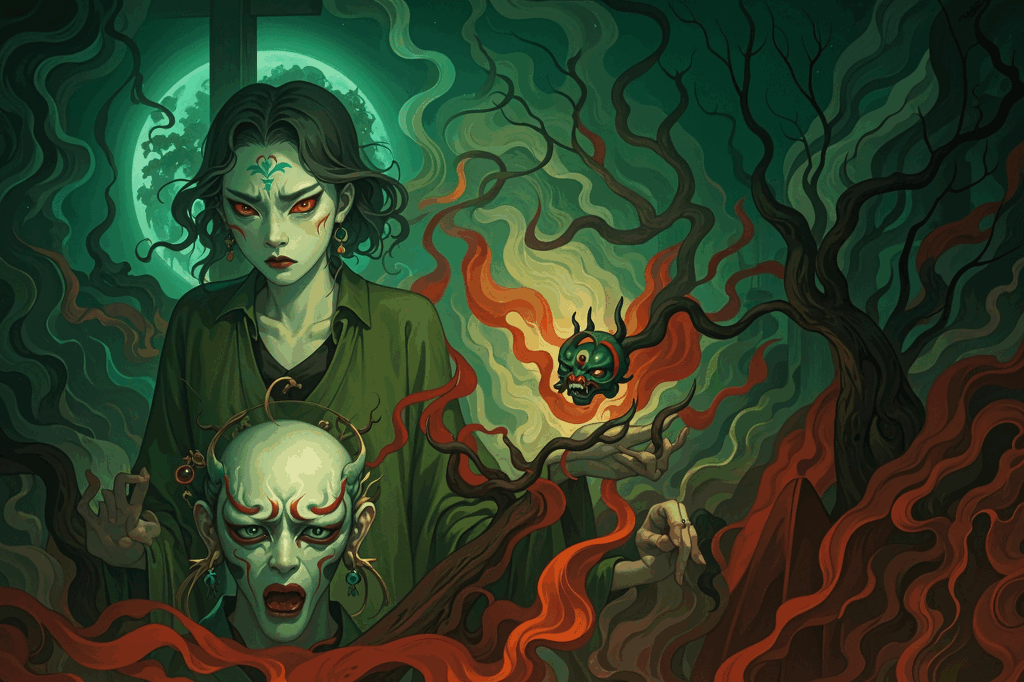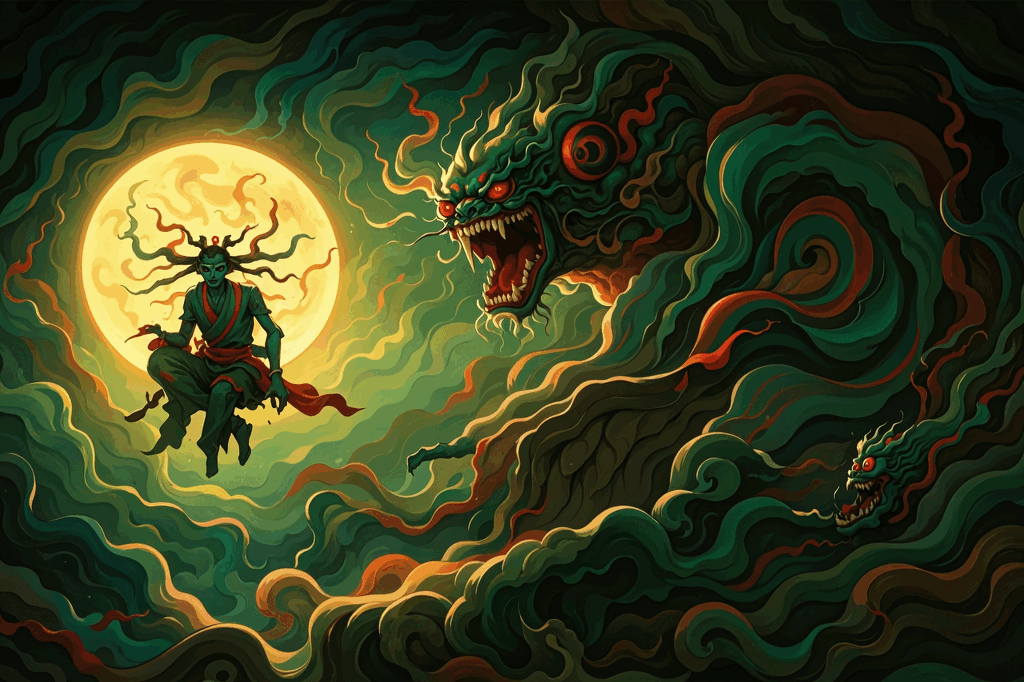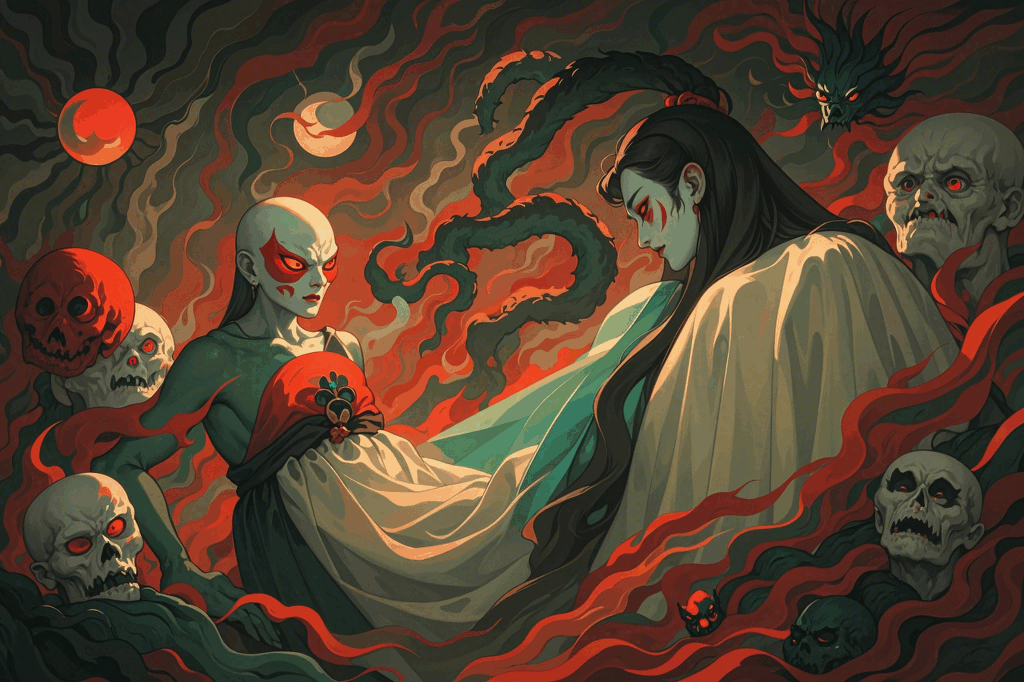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县很多乡镇的人成为深圳的第一批工人,到深圳淘金,而同时也有部分人心怀不轨,跃跃欲试,暗中觊觎这些打工者沉甸甸的口袋。当时粤东人从深圳回家,坐长途汽车必经海陆丰,而那里则成为很多回家的打工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绝对不是夸大其词之说。特别是在过年前,作案者更是目无国法,肆无忌惮,经常听说海陆丰路段的一些饭店、顾客服务区,甚至偏僻的公路处发生拦车抢劫案件。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次,一帮劫匪持枪抢劫了一辆小轿车,而这辆小轿车的主人据说是当地名人,公安机关雷厉风行,在案发后一月内,抓获此劫匪团伙成员8个,此案迅速告破。这批劫匪大部分以“持枪团伙抢劫”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重刑。
十余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罪犯自己,当然也包括罪犯的家属,过去的一切,无法逆转!
十余年的铁窗生涯已经过去,时间悄悄地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昔日的英俊小伙转眼已经进入而立之年,再加上铁窗里的艰苦生活和西北的恶劣天气,让服刑者备感沧桑。一天傍晚,夕阳西下,一个身影出现在我镇的伯婆坳路口,他东张西望一番,望着物是人非的一切,感慨良久。在他眼中,最大的改变是我村的公路。因为此时我村的公路已经开通,跟镇的主干道接上,想当年他走时可还是丛林小路一条呀。乡村公路一般为减轻陡峭程度,都是绕着山岭圈子,一层层下来。平时村民照旧走小路,可以减少很多路程。他从伯婆坳的岔口开始走,凭着10多年前的记忆,仍知道怎么走这条小路,便朝着这条路走来。
离别10多年,家将是什么样子?父亲应该也有六十好几了吧,大哥、二哥的小孩估计也很大了吧,屋门前那口井还存在吗?如果当初自己能顺利考上大学,或许现在回来已有一官半职,但现在是……他很想快点回去,想尽快知道家乡的一切,但又不想回去,他害怕面对自己的亲人,害怕面对那些淳朴善良的村民,最重要的是,自己回来后将如何重新开始生活,种田吗?耕地吗?烧炭吗?养蜜蜂吗?走着走着,这男人已经进入了我村的范围,他看到小路上有一块稍微高的大石头,站了上去,向村子眺望,整个村庄映入眼帘,一阵微风吹过,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顿觉心旷神怡,自言自语道:“自由真好!”
这男人叫天古,样叔的小儿子,曾经的罪犯,未来的百万富翁。
天古在大石头上站了许久。或许累了,或许需要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他在大石头上坐了下来,闭目养神,待了一个多小时。他这么做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等到天黑,只有天黑,自己才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家人与村民。在这时间内,山路寂静一片,没有其他村民经过。不知从何时开始,不远处的对面山上传来阵阵微弱的喊叫声,双目紧闭的天古立即从沉思中惊醒,细细分辨声音,竟然是“哎哟、哎哟”的呼叫声。
不好,有人受伤了吗?天古立即站起来向对面望去,发现不远处的一棵树竟然剧烈地摇动起来,树上的叶子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天古从石头上跳下去,毫不犹豫地朝对面山奔去,可是,上对面山必须从这边下坡到底,然后再往上爬,当他到达山脚时,发现山脚到处都是荆棘,根本没有上去的路。此时,上面的声音越来越急促,“哎哟、哎哟”的叫声不绝。就在他无计可施的时候,离山脚很远的一潭死水中闪出一道灵光,向他的眼睛射来,让他眼花缭乱,天古没有感到丝毫的害怕,相反,巨大的好奇心促使他立即朝发光处跑去。地上坑坑洼洼,一不留神,一只脚踩踏了进去,顿时淤泥四溅。他想抽出那只脚,却发现脚底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感觉到是一包蜡纸袋,他用脚趾把它夹了出来,原来是个红色且密不透风的蜡纸袋,他有种莫名其妙的冲动,不顾蜡纸袋的肮脏,立即拾了起来,用力撕破,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沓厚厚的信件,他拿出第一封,惊得目瞪口呆。
10多年前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怎么会在这里?竟然完整无缺地保存在这里?父亲?一定是父亲!他朝着刚才发出声音处张望,可是,周围静悄悄的,刚刚“哎哟”的声音似乎不复存在!他呆立原地,随即抽出了里面一封陈旧的信件,收件人是自己—天古!此时的天古觉得天旋地转,一封、两封……收件人都是自己,却没有地址。他抽出了其中一封,父亲那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天古,你还好吗?能适应大西北寒冷的气候吗?天古,有人说,去那边服刑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安全回来,你会回来吗?天古,你还活着吗?……”
天古的眼眶湿润了。“天古,天古……”父亲那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回响,父亲那亲切的音容笑貌仿佛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他情不自禁地轻声呼喊起来:“爸,爸!”也不知道是自己掉下的眼泪,还是手中的污水玷污了信中的笔迹,纸上的字迹竟然慢慢地模糊起来。天古立即反应过来,这是意外收获,也是最珍贵的东西,他把手上的水滴擦干,小心翼翼地把信件叠好。此时,他最想见到的人是他的父亲,归心似箭,走,快点回家。
刚想离开,那缥缈的“哎哟”声再次传来,不过叫声已经非常微弱。不知道是不是天古太过思念父亲,他觉得那声音就是父亲发出来的,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他身上油然而生。让他觉得意外的是,死水潭的上方有一条稍微光秃的小路延伸到山上,他立即把手中的信件塞进口袋里,然后朝小路走去。
小路两边杂草丛生,越朝上走,越觉得古怪,下面原本宽敞而光秃的小路,走到中间竟然没有了!但是声音确实是从上面不远处传来的,似乎越来越近,无论如何也要上去看个究竟,于是,天古放慢脚步,循声走去。
忽然,他感觉到后面有脚步声响了起来,似乎有什么东西跟着自己,他果断地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脚步声却已经消失。他又迈步,后面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林间显得幽暗,后面的脚步声似有似无。不,永远不要朝后面看,这是天古的原则,据说这也是所有从监狱里走出来的人的共识—不要向后看!
他不再理会是否真的有什么东西跟着自己,只管朝前面攀爬,其间,他几次被一些树枝绊倒。他毫不在意,最后爬了上去。他眼前一亮,奇怪的是,这里是个大坪,靠近山壁那边,竟然是个窑洞,也是曾经烧炭的地方!
这是一个废弃的窑洞。窑洞的上方裂了几道痕,看来许久没有人在此作业了。天古站在大坪上,转身朝原来的方向看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可是,明明声音就是从这边传出来的,怎么就是不见人呢?
天古朝着窑洞走去,喊道:“有人吗?”
微弱的“哎哟、哎哟”声音似乎从窑洞中传来!果然有人,天古一头扎了进去,眼睛在瞬间没有反应过来,他只觉得眼前漆黑一片。他没有继续往前走,只是问道:“是谁呀,你在哪里呀?”窑洞内沉寂一会儿之后,声音再次传来。天古发现声音是从身边墙壁上发出的。天古在黑暗中轻轻地敲打着右边的墙壁,然后屏气聆听里面的反应。让他觉得怪异的是,墙壁竟然微微震动,接着传来了轻轻的拍打声。他疑惑片刻,立即知道窑洞外面的右边有人,他匆忙转身跑了出来,在黯淡的光线下,发现地面上蜷缩着一个身影,穿着蓝色的土布衣服,身子倚靠着窑洞的墙壁,背对天古,天古无法看清那人的脸,但看着那人的身影,跟父亲非常相似。他情不自禁地大声叫了起来:“爸,爸,是你吗?”一边喊,一边跑了过去,蹲了下来。可是,刚刚接触到此人,天古就惊呆了。
此人的下半身竟然被一个庞大的树干压住,根本无法动弹,更让天古震惊的是,他靠近此人的时候,自己浑身发抖,接触此人的瞬间,就觉得对方的躯体异常冰凉。此人艰难地扭过头来。天古不寒而栗:这难道是父亲吗?不,父亲不是这个样子的。此人面无表情,满是凝固的黑色血迹,面容格外吓人。
天古声嘶力竭地喊道:“爸,是你吗?我是天古啊,我回来了啊!”老者微微地点头,露出了一丝微笑,欣慰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听老者这样说,天右更加坚信这位老者就是自己的父亲,天古想挣扎起来搬走压在父亲身上的树干,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站起来。老者看到天古想站起来,举起那只有气无力的手臂,示意天古别走。只见老者轻轻地拍打着窑洞的墙壁,一句话也没有说。天古大惑不解,他实在看不出窑洞墙壁有什么问题,正在疑惑之时,窑洞左上方的路口闪出了一个人影。
天古放下父亲,发现自己可以顺利地站起来,他朝男人走了几步,然后焦急地向那人大喊道:“快来,救救我的父亲!”此人向前走了几步,站在天古的面前。这时的天古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个中年男人,个头不大,肌肉却非常结实,看他的装扮,是个砍树的或者是个猎人。天古不认识他,料想此人不是我村的。
此人听了天古的话,疑惑地望着天古,然后不紧不慢地问道:“你是个外地人吧?”
外地人?天古恍然大悟,悲哀啊!他这才发现刚刚跟这男人说话时自己竟然用了普通话,10年的监狱生活,已经习惯性地改变了自己说话的口音。他情急之下想用客家话表达,却根本无法说出来,他用半生不熟的客家话结结巴巴地说道:“不……我……是××村的!”
那中年男人听了,仍是将信将疑,然后上下打量着天古,说道:“那你刚才怎么说起了普通话?”
天古实在不知如何解释,他大叫起来:“这个迟点跟你说,快过来,救我爸爸要紧。”说完,就带这男人过去。可是这男人仍没有放下心中的芥蒂,一边走一边嘀咕道:“你爸爸?这里会有你爸爸?”
走过去的天古大叫一声:“啊,人呢?”就在他大叫之后,窑洞旁边的那棵树上一只鸟飞走了,瞬间树上掉了不少叶子。原来地面上是一条硕大的树干,窑洞旁边,一件破烂不堪的土布衣服挂在那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天古有点怀疑自己是坐牢坐出毛病来了,大脑不好使了。他双手抱着自己的头部,大喊道:“不,不,这不可能!”
中年男人问道:“年轻人,你没有什么事吧?”
天古没有回答,他偷偷地摸了摸自己口袋中的信件,发现信件安然无恙,这不可能是假的呀?
估计是中年男人无意中瞟见了天古口袋中的红色蜡纸袋,忙问道:“你是不是捡到了什么东西?”
天古双手一摊,急忙道:“没有呀。”
中年男人似乎不太相信天古,说道:“这个地方,不是你一个外乡人可以乱来的,你好自为之,最好不要装模作样,早点走吧。”说完,带着工具离开了。
天古如痴如醉,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天色也不早了,他回头看了看窑洞周围的地形,一声不吭地朝山下走去,到了小路口,朝我村走来。他回头时发现那个中年男人站在那块大石头上窥探他。
天古要想回到自己的家中必须经过村头那几个寨子。还好,走了半个小时,到达村头时,天已经黑了,没有人跟他搭讪。他顺利地回到了村中自己老家的寨子。
在寨子的门口,他在那口熟悉的井边徘徊了一阵,可是那口井的周围堆满了生活垃圾,井口也被塞死。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我村的各个寨子都已经接了水管,直接把后山的泉水引到家里。然而,后面的变化比这大多了。
当时只有路伯一个人坐在寨子门口,是路伯,天古觉得面熟,却一时半会叫不出口,路伯惊愕地看了一会儿天古,然后惊讶道:“你……你是天古吗?”
天古迟疑片刻,说道:“是的,你是……路伯……吧?”他走过去紧紧地握住路伯的手。路伯大体没变,只是比以前老多了,皱纹布满了额头,青筋凸显,头发白了一大半。天古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些小孩子走了过来,眼前的这些小孩,没有一个是天古认识的。这时走过一个年轻妇女,天古也不知道是谁的媳妇。眼神很好的天古看到大堂屋檐下的路伯母,刚想跟她打个招呼,却发现路伯母脸色不对,她故意避开自己的眼神。
天古刚和路伯闲聊了几句,发现身边的小孩子都被家长喊了回去。上堂屋檐下汇聚的人越来越多,天古变得特别敏感,从家长喊小孩声中,天古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这时,他听到了几句窃窃私语的议论。议论声中,下面几句尤其刺耳。
“这不是天古吗?都说他死了,怎么还活着呀,不是说去西北服刑的人员不可能回来的吗?”
“天古,他不就是样叔的儿子啊?听说他坐牢,是因为他爸爸曾经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呀,曾统不就是被他爸爸害死的嘛!”
“你呀,你呀,小孩子那么好奇干什么哦?别过去,不要跟坐牢的人走那么近,小心你以后也学坏!”
天古没有理会他们的闲言碎语,其实他早料到会出现这一幕。这也不怪他们,只能怪自己,自己走上邪道,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他强忍着泪水,向上堂屋檐下黑压压的人群望了望,露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然后他哽咽着对路伯说:“路伯,迟点再聊,我先回屋子去了!”
路伯却紧紧地拖住天古,说道:“天古,你家的房子已经没有住人了。”
天古立即呆若木鸡,站立在门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许久,才轻声地问道:“为什么?”
路伯语气沉重地说道:“你大哥他们搬到新四寨那边住了,你二哥几年前移居外地了。”
天古毫无表情地问了一句:“我爸爸呢?他也跟我大哥一起住吗?”
路伯没有立即回答,他认真地注视着天古脸上的表情,叹了口气,突然话锋一转,说道:“天古,你还没有吃饭吧?来,去我家吃饭,咱们慢慢聊。”说完拉着天古的手想走。
天古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声音低沉地问了一句:“路伯,我爸爸他究竟怎么了?”
其实,不用路伯亲口说,天古已经想到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他仍然抱着一丝的幻想,坚持要路伯亲口告诉他。路伯迟疑了一会儿,说道:“看来你还不知道吧,你爸爸在3年前过世了!”
天古顿觉头脑一片空白,摇头喃喃道:“不,不,怎么会这样?他还那么年轻呀!”不过他很快沉默了,默认这个令他痛心万分的事实。这一点,或许只有改造过的人才做得出来,这也是他后来成功的要素之一,他可以在瞬间把所有的痛苦都吞到肚子中去。
路伯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说道:“天古,人都有一死,你就别伤心了。你还是先到我家吃饭吧,走!”
天古对路伯的盛情邀请表示了感谢,然后说道:“我还是先去我哥家吧,你刚才说新四寨,对吧?”
路伯急了,他斩钉截铁地对天古说道:“天古,你还是暂时不去你哥哥家好!”
听到路伯话中有话,天古一脸疑惑地望着憨厚的路伯,希望从路伯口中得到答案。路伯把天古拉到自己房间中,不厌其烦地解释道:“天古,实不相瞒,因为你的事,你们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你去东北,哦,是西北,对吧?一两年都没有你的消息,大家都说你去那边摘什么花,空旷的地方连锁都不用锁,你根本无法逃走,冻死你。村里人都认为你不可能活着回来,连你哥哥也这样认为,后来你大哥结婚了,闹着要分家,你爸爸却不肯,说要等你回家再分。但你大哥却说你们家中已经没有你了,可是你爸爸态度很坚决,你大哥拗不过你爸爸,大吼大叫,说先不用理你,先分掉家中的山林田地,万一你侥幸不死回来了,再作打算,你爸爸迫于无奈同意了,于是山林田地给你两个哥哥瓜分了。你大哥根本没有想到你会活着回来,我想你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听完路伯的话,天古并没有恨得咬牙切齿,他只是摇头一笑。这让路伯摸不着头脑,路伯紧张地说:“天古,你不会去报复你大哥吧?我可是凭良心说话呀,你可不要那么做呀,我可不想挑起你们兄弟之间的争执呀!”
天古淡淡地笑了笑:“路伯,你放心,我不会那么傻的。”
听完天古的话,路伯稍微放下了心,说道:“天古,去我家吃饭吧,很多事情我们吃完饭再谈。”
虽然路伯盛情难却,但天古还是推辞了。据后来天古讲,他知道路伯是出于一片好意,但那个连招呼都不打的路伯母呢?对这一切,他心知肚明。天古笑着说道:“暂时不用了,我还是回老房子看看吧。”
路伯疑惑地问道:“你有钥匙吗?钥匙可在你大哥手上哦。”
天古说道:“我不用钥匙,不就是个木门嘛,一撬就开了。”说完,他走出路伯的房间,穿过走廊,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他久违的家门前。
30年前,天古就是在这间房子里面出生的,十余年来,他没有回来过。这个夜晚,他回来了,此时家门紧锁,锁头生锈,门框两边连一副陈旧的对联也没有,里面那个最熟悉的人已经过世,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什么牵挂呢?他没有马上撬门,而是呆呆地站在房门面前痛哭!
当年,母亲死去时,年幼的他不知道哭是何滋味;当年错过上大学的机会时,他没有哭;被宣判时,他没有哭;甚至被狱友残酷地殴打时,他也没有哭;而那一天他却对着门框痛哭起来。左邻右舍听到了哭声,却没有一人上前劝慰,这究竟是世态炎凉还是人情凉溥?他无暇顾及!哭吧,彻底地痛哭一次吧,哭不是懦弱,哭不是屈服,痛定思痛之后会是彻底的重生!
不知过了多久,身心疲惫的他从屋檐下的一捆柴中抽出一根大木棍,从门槛与门缝之间的缝隙塞了进去,向上用力一撬,房门被撬开了,一股浓烈的霉气扑面而来。天古拉亮灯泡,房间内布满了蜘蛛网,原来放置床的地方却只留下两条木凳,上面积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接着他来到后屋,看到了那把熟悉的竹椅。这是一把多功能竹椅,在夏天时,可以搬到屋檐下,抽出下面的一层,当做睡椅。曾经,在大夏天的晚上,屋檐下凉风习习,父亲躺在竹椅上,为坐在小矮凳上的自己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而现在,竹椅仍在,父亲却已离去。他缓缓地坐到竹椅上,不经意地在屁股上一摸,却发现一点灰尘都没有!
父亲没有死!这是天古第一时间的想法。他立即跳了起来,可惜的是,他已经破坏了第一现场,他细看这张竹椅,发现竹椅干干净净的,不像尘封很久的东西。父亲肯定经常来坐,不然为何竹椅如此干净?天古激动起来,兴奋地叫道:“爸,爸,你在吗?”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回应。
突然,后屋的窗户“咣当”一声,像是什么东西钻了出去,原本挂在窗户上肮脏的窗帘布飘动了一下,而后,房间里仍然静悄悄的。天古急忙跑到后窗前,朝外面喊道:“爸,爸!”没有任何回应。天古有气无力地坐在竹椅上,陷入了沉思中。他感觉到爸爸走到竹椅旁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缓缓地说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天古,天古!”突然,有人在门外喊叫,这惊醒了天古,天古立即从竹椅上站起来,急忙跑到门前,叫道:“爸,爸。”门外是路伯。路伯端着一只大碗,里面放着几个大芋头,走了进来,关切地说道:“天古,很饿了吧,吃了这几个芋头吧,槟榔芋,很甜的。”
天古不再客气,抓起芋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地,一碗芋头一扫而光。
吃完后,路伯叫天古去他家洗个热水澡,这样舒服点。天古却突然说道:“路伯,我觉得我爸没有走,我刚才都感觉到他回来了。”
路伯环顾四周,狐疑道:“真的?”
天古肯定地说道:“真的,路伯,不骗你,我看到竹椅上一尘不染的,这不可能吧!”
路伯惊讶地“啊”了一声,哆哆嗦嗦地说出两字:“竹椅?”然后他端着碗走出了房间。
到门口时,路伯扭头对天古说:“天古,等下来我家洗澡。”然后匆忙离开。天古见路伯如此怪异,断定路伯知道些什么。待了一阵,天古去路伯家洗了个澡,回到家中,躺在竹椅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天古去新四寨找大哥。
经过寨子中人的指点,他径直来到大哥的家中,一个年轻妇女刚要出门,天古走上前去,问道:“实哥呢?”
这妇女上下打量他,然后回头向里喊道:“阿实,有人找你!”实哥走了出来,一下震惊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弟弟还可以回来。此时的天古,不再期待着激动的拥抱,也没有失声痛哭的冲动。果然,实哥淡淡地说了一句:“咦,回来了?奇迹啊!”
其实,按理讲,村庄如此小,消息传播速度快,在前一天晚上,天古归家的消息应该已经传到实哥的耳中。当晚实哥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欢迎弟弟的归来,这种行为不言而喻。天古心中有数,淡淡地说道:“是的,哥,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活着回来。”
那个妇女听天古如此说话,已经明白了天古的身份,走了过来,高兴地嚷道:“原来是小叔天古,对吧?快进来坐,快进来坐呀!”天古没有进去,他的心情像打翻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嫂子的热情与实哥的冷淡让天古感慨万千。旁边3个小孩不约而同地跑了过来,都惊讶地看着天古。实嫂对这几个小孩说:“这是你们的叔叔,快叫叔叔!”
实哥飞快地拉住走在前头的一个男孩,恶狠狠地对老婆骂道:“你呀,你会不会教育小孩?我没有这样的弟弟!”实嫂不知如何是好,她悄悄地对实哥说:“你怎么能这样啊?好歹也是兄弟啊!”
实哥狠狠地对老婆瞪了一下,估计实嫂早已吓得屁滚尿流,一句话也不敢再说了。这一切天古看在眼里,安慰嫂子说:“阿嫂,不要为我的事操心,是的,我不配做他的弟弟。”说完转身就走。
实哥没有对天古表现出丝毫的怜悯,他没有挽留弟弟,只是冷冷地说道:“你稍等,我去拿老屋的钥匙给你。”天古没有停下脚步。还要什么钥匙呢?昨晚都已经破门而入了。
其实,并非所有的村民对曾经的犯罪分子如此避而远之,也有人主动上前跟天古搭讪。只是,被亲哥哥彻底抛弃的天古已经彻底死心,被逼上梁山的他深深知道自己只有尽快自食其力。
离开哥哥家,并不表示天古无路可走。他回到原来的老房子,从杂物间掏出一些旧的锅碗瓢盆,再加上现成的灶头,轻而易举地开伙了。在路伯的带领下,一些好心的邻居,据说也包括偷偷摸摸的实嫂,陆续送来了一些萝卜、咸菜、番薯之类的东西,至此,温饱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在老房子住了几天后,天古发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天黑之后,除了路伯会在自己房前走廊经过,其他邻居要出去的话,都显得神神秘秘的,绕其他走廊而走,显然,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这让天古更是觉得满头雾水。
一个晚上,天古突发奇想—邻居们的举动应该与父亲的去世有关吧?想着想着,他听到门外不远处传来了邻居家两个小孩的说话声。
姐姐说道:“不要走那边,直接从这里出去呀!”
妹妹压低声音答道:“等下又会听到样叔公回来的动静,怎么办?”
姐姐说道:“天叔都回来了,还怕鬼吗?他现在都在里面住了,从这里经过,没事的。”
天古觉得很奇怪—难道父亲阴魂不散?难道这里的房子经常闹鬼?他立即想向邻居女孩问个究竟。于是,“吱嘎”一声,他把门打了开来。就在开门的瞬间,小女孩子发出一声惨叫:“鬼来了!”
走廊上灯光不足,但天古仍然把邻居女孩家的妹妹看得清清楚楚,他立马走上前安慰道:“婷婷,别怕,是我呀!”但是,估计婷婷吓得不轻,仍然哭个不停,旁边的一些邻居也走出来了,其中有婷婷的母亲和路伯。婷婷母亲赶忙抱住停停,嚷道:“哎哟,谁叫你从这里经过呀!”然后就抱走了婷婷,一些人也陆续离开。天古立即逮住路伯,把路伯邀请进房间。
天古迫不及待地问道:“路伯,这是怎么回事?你可要说实话呀!”
路伯不慌不忙地坐在一把矮椅上,朝里屋望了望,语重心长地说:“天古,我跟你说,路伯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你以前是走错路,确实也有些人对你有成见—人家对你有看法也在所难免,但是,他们很少从这里经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呀!”
天古低声问道:“是什么原因?”
路伯神色凝重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咳嗽一声,故作镇静地说:“自从你爸爸走了,这个房间不是很太平呀,好几次晚上有人经过,都听到那张椅子发出摇晃的声音。那张椅子不是你爸生前最喜欢坐的吗?所以大家都特别害怕,特别是半夜三更的,一个人时都不敢从走廊前面经过呢,就是害怕听到那个声音。还有呀,有一次,不知是谁,经过时,看到里面的灯泡亮着,门是锁着的,听到了你爸爸的叹息声呀。”
天古听了路伯的话,喃喃自语:“难怪,难怪,我总是感觉他还在一样。”
路伯叹了一口气:“我想也是,你爸可能阴魂不散呀,主要是为你呀,担心你呀,他一直等着你回来呢。没有想到,你现在回来了,却跟他阴阳相隔啊,我想你尽快去他墓地拜祭一下,告诉他你回来了,估计他在九泉之下也会安息了。”
天古听了路伯的话,心中酸楚,许久才问道:“我爸他埋在哪里?”
路伯愣了一会儿,说:“难道你哥没有告诉你吗?就在筒子岗你家那爿山上。”
天古点了点头,说:“好的,我会尽快去拜祭一下,多谢你,路伯。”
路伯挥手道:“呦,呦,呦,别客气,左邻右舍的,说这些干什么呢?对了,你爸真的很关心你,他可是因为你死不瞑目呀!你知道吗?你爸爸出事时,被抬回家中后,据说当时他希望自己死后被埋在烧炭的那座山呀,我想他的意图很明显呀,就是为了可以看你回来,不过那年不利那个山头的方向,所以没有葬在那里。据说他生前去那里承包山来烧炭,目的也是为了等你回来呢,那个烧炭的窑洞呀,地理位置好,居高临下,如果有人走路去村中,在那里都可以看得到的。”
什么?天古顿时瞠目结舌,他终于明白了,路伯说得一点也没有错,父亲确实等到了他回来,天古第一天回来时,那个暗中接待他的满脸是血迹的人就是他的父亲!据说,样叔出事时,就是被窑洞旁边的树干压住了。
第二天天古立即去父亲的坟墓拜祭。拜祭完之后,天古感到非常失落。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怅然若失。他开始思考自己该干什么。天古荒废了10年的时间,又没有一技傍身,感觉前途渺茫。路伯给他指引了一条非常光明的道路—烧炭。子承父业呀,最重要的一点,当时天古父亲承包的山还没有到期,他照样可以去原来的地方烧炭。
当天古来到邻村找到那座山的主人时,他惊呆了,父亲承包的山的主人就是天古归家当天碰到的那个中年人。中年人见到天古之后,也觉得非常意外。详谈之后,中年人才知道样叔还有这么一个儿子。据说,多年前样叔向他承包此山时,对于承包价格,样叔非常豪爽,山主人当时还怀疑样叔是否有点愚笨。后来中年人经常路过时,都看到样叔站在窑洞门口朝对面的路口张望,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现在看来,一切都是为了天古!
对于天古欲来此山烧炭的想法,山主人大力支持。于是,天古的烧炭生活正式开始。不过,开始也面临着结束,后来,天古讲当年的烧炭史时常说烧炭半年,那是夸张的说法,每个成功人士在说起当年的创业艰辛时,都会绘声绘色地增加很多神秘和夸张的因素,其实他真正烧炭的时间也就十五六天。在此期间的最后一天,出事了。当时的事件肯定是真实的,只是最后的结果,无人知晓!
事发的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当时,天古做烧炭工人才十几天,在做前期准备工作,修葺窑洞、砍树等。他砍了一些树,觉得很累,躺下来休息,刚刚躺下,就发现一只杆伦(客家话,类似于老鼠的小动物)从身边快速蹿过。他顿觉眼前一亮,这玩意儿,那可是好东西。前些天出门上山前,路伯特地叮嘱过,说他媳妇身子不好,如果天古上山烧炭,发现有杆伦,可以捕杀回来呀,那味道可是相当鲜美的。
他奋起直追,但是要在山上捕捉老鼠之类的小动物,谈何容易?这只杆伦跑动敏捷,一下蹿到了窑洞的右边墙壁上。而在不远处追过来的天古,却是赤手空拳。他找到棍子之后,看到杆伦爬进了一条缝隙中。天古顿时喜上眉梢,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杆伦跑动时,不容易被抓住,现在它钻进裂缝了,抓住它却易如反掌。
天古立即从路旁拔来一把干草,捆成一团,用火柴点着了,发出浓烈的烟雾,靠近缝隙,烟雾飘进空隙,可是,杆伦并没有爬出来,只是发出“叽叽”的鸣叫。天古立即拿了一把锄头,挖开了,他惊呆了,杆伦被熏得晕晕的,呆呆地蜷缩在洞里,但是颜色颇为怪异,竟然是红色。天古不管那么多了,伸手去抓,却发现那东西竟然不会动。
正在此时,山主人出现了,对天古喊道:“天古,抓什么东西啊?”天古迅速地把手中的那包东西塞进口袋里面,估计他被烟雾呛了一下,咳嗽着走了出来,回答道:“抓杆伦呀,跑了!”
山主人看到了天古的小动作,上前问道:“天古,你捡到了一包红色的东西啊?”
天古双手向前一摊,说道:“没有呀,没有抓住,跑了!”
山主人疑惑了一下,然后跟天古在大窑洞前坐了下来,两个人抽着烟。山主人忧心忡忡地说:“天古,有件事让我一直难以释怀呀。”
天古大吃了一惊,直愣愣地盯着山主人。山主人解释道:“你爸出事时,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当时他拿了一包东西给我,是用红色蜡纸袋包住的,里面好像是信件,说要交给他的儿子,现在看来应该是要给你的!唉,我当初确实从你父亲手中接过来了,然后匆匆忙忙下山去找人来现场,刚刚跑到下面的山脚,来不及刹住,一个踉跄摔得我四脚朝天,那包东西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丢了。当时我想人命关天,还是先去你村找人,那东西慢慢再找。可是后来都没有找到,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你哥哥,后来上山时,我都会留意一下,只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以为你刚才捡了那包东西……”
天古从地上站起来,灵机一动,感激道:“原来这样,这包东西我当天回来时在山脚下捡到了,里面是信件,确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是父亲对我的一片情意啊!”
山主人听了,久久不能言语,叹道:“你父亲确实在天有灵呀!”至于此刻山主人内心是否有其他阴暗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很多事情。在谈话中,天古显得心不在焉,因为他刚刚又得到了一包东西。他迫切地想知道,冥冥之中父亲赐予自己的这包东西又会是什么呢?当然,他很快就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只是,具体是什么,村中之人,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
半个月后,天古告别了短暂的烧炭生涯,去珠三角闯荡。大家放心,重生的他,此番闯荡走的是正道。当时的呼机开始刚刚兴起,叫银河通信的96169就是他创建的。为此他赚得了第一桶金,开始了他的财富人生,短短几年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便进入百万富翁的行列,在我村非胡润富翁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可是,对于天古的飞黄腾达,很多人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他的启动资金来自哪里?刚刚改造出来的他,怎么会有原始积累资金呢?或许他哥哥的提示给了我们一种猜测。在天古发达之后,他的哥哥总是在烂醉如泥之后苦笑着说,父亲对弟弟偏心,偷偷把家中什么祖传的东西留给了天古……
天古却不太理会大哥的一相情愿,回闹鬼村祭祀先人时,他仍一如既往地在父亲遗留的老房子里开伙。